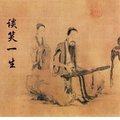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挑战与反应,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自从骑马术发明以来,分布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从兴安岭到匈牙利——的游牧民族,凭藉著骑射的优势,一直是周近农耕社会最头痛的敌人。十七世纪以後,满清与俄国倚恃枪炮之利,向内陆亚洲扩张,才把这些在黄沙白雪中熬练出来的“天之骄子”的气焰压制下去。
以我国北部蒙古为中心的北亚草原地带,是世界大草原的一部份,也是近代以前整个草原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主要的动乱摇篮。二千多年来,游牧民族无数次的移民运动与对外侵略,多肇源於斯,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影响及於远方的定居社会。我国更首当其冲。北亚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可说是我国历史形成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什麽是促使游牧民族侵袭农耕社会的原因呢?这自然是古来众所关心的一大问题。中外学者企图对此问题作一解释者甚多。大体说来,过去学者偏重由人性和自然环境等角度来寻求答案。近年来,学者多从经济的观点着眼。事实上,几千年来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相互反应,是一极为繁复的历史现象,单从一、二角度去分析很难得到真相。
本文旨在对中外学者所主张的各种说法作一较有系统的评介,以求对这一问题获得比较全面的印象。例证的范围虽以北亚游牧社会与中国农耕社会为限,但以下胪列的各种原因中有二、三项也可适用於其它地区。游牧民族的侵略农耕地区,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无法把北亚和东亚地区完全孤立来讨论。
各家主张,虽有歧异,但多肯定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各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因而产生不同性质的社会;其中之一,由於环境的压力和经济的需要,不时侵入另一社会。因而;在介绍各种解释以前,先将游牧经济的特质——尤其是造成他们向外侵略的各种质素,略加剖析,以助了解。至於北亚的自然环境是众所周知的,不再辞费。
北亚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主要建立在“逐水草而迁徙”的草原游牧制上。这种草原游牧与牧场畜牧制不同,既不栽培牧革,也不储备乾草以待乾旱或雪寒,却高度仰赖自然,顺应季节的循环而辗转於夏季和冬天的牧地之间。这种草原游牧经济的特色之一是,对自然变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极为敏感。草地对牲畜的包容力随气候而增减的幅度之大,实超出我们农耕社会人民想像力之外。换句话说,在一定面积的牧地上,如遇气候良好水丰草美,几年之内畜群便可增殖一倍以上。如雨量减少,牲畜必因乏草而大量死亡。此外,对于瘟疫、风雪等意外,也缺乏适当的应急办法,牲畜死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史记说,天灾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伍”,绝非夸大。因而,游牧民可能在短期间丧失原有的生活资源,必须另辟蹊径,谋取生活。同时,当於牲畜是游牧社会的主要财富,牲畜的丧失便是财富的丧失,因而游牧民极难於聚积财富。
第二、北亚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有跟农耕社会达成“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的必要。从表面看来,北亚的游牧营帐是比较自足的经济生产单位,它们同时放牧几种动物;如羊、牛、山羊、马、骆驼等。这和西南亚游牧民以一种动物为主要生产凭藉者不同。这种多动物的游牧方式,几乎供给了游牧民衣食住行必需的资料。而且,由于各游牧营帐所产大体相同,故无相互交换的必要。不过,游牧社会虽无对内交换的必要,却有对外交换的需求。
北亚的游牧制度是一种甚为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经济体系里,畜牧占了主要部份。虽然匈奴、突厥和蒙古都留有发展农业的痕迹,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量显然微不足道,这和西方的游牧经济不同。阿尔泰山以西的突厥民族,伊朗及阿剌伯人等,往往在一河谷或绿洲之中同时拥有畜牧和农业两个生产单元,两者密切接合、维持共生关系。北亚的游牧社会中别无足以平衡游牧单元的农业单元,而与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形成一个广大的经济共生区。
游牧社会必须与农业社会交换乃是由於下列的原因:一、他们有取得农产品的需要。游牧民虽以“食兽肉,饮其汁”为主,但至少自匈奴以来,游牧民——尤其是贵族——即有以米谷佐食、酿酒的习惯。这种对农产品的需要量,不是草原上稀疏的灌溉农业所能供应。二、游牧贵族需要若干高水准的工艺品来增益他们的生活内容。工艺技术只有在安定和长远的基础上才能发达,在着重流动性的游牧社会裹,工艺技术的发展甚为有限。许多维持较高生活水准的必需品,都是游牧社会不能自行生产的。例如:绢织品、麻织品及若干金属器具和饰物,都须自居国社会以交换或掠夺的方式去取得。三、在草原经济繁荣时代,游牧民族必须向农耕社会推销过剩的畜产品,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而通常为人忽略的因素。农业社会主要的财富是土地和粮食,土地既有较固定的价格,又不会因天灾或兵燹而毁灭;游牧社会主要的财富则为动物,动物在恶年会死亡,丰年时则因过剩而普遍贬值。所以,凡在草原牲畜繁衍时,游牧民必须以之向农耕社会倾销。
以上述各因素为背景,现在讨论关于游牧民族何以不时南侵的几种解释:
第一种是天性嗜利说。这是农业社会中传统的看法。我国文书中可寻出许多这类例子。如史记说匈奴人突厥名臣敦 * 谷( tunyukuk )认为:突厥之能够以劣势与唐长期周旋,在於「强则进兵抄略,弱则窜伏山林。」这都表示游牧民族在贫弱时,或则求和,或则逃匿,而不大规模地侵略。内田吟风教授曾分析公元前二 O 九年至公元後九一年间匈奴入侵的纪录;结论为:凡匈奴发动战争时,国内都无饥馑现象;反而有九次因饥荒而退兵求和。不过,如因人口膨胀或自然灾害而形成饥馑,草原边缘的小股游牧民被迫挺而走险,侵袭中国边境的农村,则很有可能。可惜这类小型的侵袭大多不见於记载。
第四种解释为贸易受阻论。近来主张这一论的学者最多。我国有札奇斯钦先生、余英时先生;美国有赛瑞斯神甫( Rev.H.serrucys );匈牙利有艾克西迪 (HildaEcsedy )氏;日本则有松田寿男、田村实造、 * 原淳平等人。这些学者或则研究汉代和明代的朝贡制度兼及贸易,或则研究隋唐的绢马贸易,或则研究明代的茶马贸易,或则研究土木之变的经济背景,或则综论几千年来的贸易和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题目容有不同,结论容有小异,但大体上都肯定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间贸易的有无跟两者间的战和有极大关系。现因限於篇幅、无法分列各家的论点,兹综述於後:
( 1 )游牧民族有向农耕社会取得若干物资的必要。这些物资可以和平的方式——朝贡与互市——取得;也可以掠夺的方式去取得。掠夺是一种无偿的贸易,但因中国边防坚强,武器优异,游牧民宁愿出之於和平的方式。武装掠夺是一种不得已的次要方式。
( 2 )无论游牧国家和农业王朝维持什麽形式的外交关系——汉初与匈奴的昆弟对等关系,宋辽、宋金的叔侄关系,或朝贡制度下的君臣关系——都蕴合着交换方物和互市的经济交换关系。游牧国家跟中国朝廷维持正常外交关系的着眼点,即在於这种经济交换。因此对游牧民族而言,接受岁币或赏赐和互市,才是朝贡与和亲的实质。
( 3 )中国对这种贸易却常不从经济观点著眼,而从政治著眼。中国古来自认为物产丰饶、无庸对外贸易。中国强力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更严格地限制了私人的对外贸易。商人与边疆百姓对国际贸易的需耍,多不为政府所顾及。政府所着重的是以对外贸易为「和戎之一术」,把它当作维持以中国「天子」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朝贡制度——的一种手段。所以,对中国而言,通关市与赏赐礼物是建立世界秩序的代价。
( 4 )中国朝廷往往由於政治设想或财政困难,而与游牧民族断绝或减少互市。在这种情形下,游牧民族唯有以武力来开拓市场。对游牧民族而言,战争和贸易是不相矛盾的。贸易是武力的目标,武力是贸易的後盾。贸易有赖军事行动来创造机会;而贸易数量的大小往往与他们所能投资的武力的强弱成正比。
这一种贸易论的看法兼顾了游牧国家的经济特质和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特质,可说触及了游牧民族与中国之间战和关系的最根本的原因。但讨论贸易之重要性者必须兼顾下述的掠夺说,始能得到较为平衡的看法;因为游牧民族之犯边,并非全由农耕国家断绝关市所引起。
第五种解释:掠夺是游牧民族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主张这一说法者有青木富太郎、护雅夫,江上波夫等人。由於草原社会的生产力不稳定,工艺技术落後,难于累积财富,而游牧民族又是尽人皆兵,所以聚众掠夺是游牧社会的一种自然的无偿输入行为,也可说是一种生产行为;藉以解脱因厄,或增益生活内涵。这种掠夺又可分为:①游牧民之间的互相掠夺,②对来往草原的队商的掠夺,②对农耕社会的侵夺。现在所拟讨论的乃是最後一类。
游牧民对农耕社会的掠夺,主要是由於受後者的物资诱惑。当游牧民族有统一的政治组织,而且兵强马盛时,常会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例如,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皆屡次违背和亲之约,侵略汉边,便是以掠夺为目标。也先( Esen )的侵攻明朝而引起土木之变,基本的动机也在於掠夺。江上波夫指出:匈奴掠夺的主要目标为①家畜,②人口,③物资。前两者是游牧民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手段(工匠,奴隶);都是正规互市中无法取得的,後者则足以增加游牧君长和平民的财富。
掠夺可说是游牧社会中无论贵贱都欢迎的一种生产方式。朝贡贸易的利润,似为可汗及少数贵族所垄断,而掠夺的战利品,则由大家所分享。这几乎是古来游牧民族一贯的习俗法。匈奴人「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趋为利。」鲜卑人「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可见掠夺是一项重要的利益均沾的生产行为,虽然酋长仍保持分配战利品的权利。
总之,贸易与掠夺是游牧民族取得所欠缺物资的两种方式,两者相辅相成,各有各的功能。掠夺是一种无偿的贸易;以武力为后盾的贸易也可视为一种变相的掠夺。至於以武力届服农耕国家,西域绿洲城市,或其它草原部落,强徵贡赋或岁币,也可视为一种长期性的、制度化的掠夺。
第六种解释是政治的,即是:对外的掠夺、贸易或战争是游牧社会从初级的氏族组织,进展到高级的部族组织、游牧帝国,乃至征服王朝的催化剂;也是游牧领袖加强自己的权力,扩大势力,从氏族长、部族长上升到游牧帝国的可汗和征服王朝的帝王的必要手段。许多学者的著作中部表露出这一看法。现在也综述於後。
赖德懋教授曾指出:一个建构在近乎纯游牧经济上的社会(纯游牧经济从未存在),它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必定较为简单与平衡。战争与贸易必然会带来经济分配关系的变化、财富累积的歧异,乃至促使部族长与平民间隶属关系的强化。因为欲求在掠夺或战争中发挥较为有效的功能,并防止敌人的报复,必须使组织扩大,军事化和永恒化。另一方面部落君长因手操战利品分配权,故可加强部民或次级首长跟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对外贸易更能增加游牧君长个人的财富与权力。这种种对外的活动,都足以弱化原有的氏族或部族组织,进而组成较为强大的部族联盟或游牧国家。
即在游牧国家成立後,由於游牧经济本身的薄弱,不足以维持广大的国家组织,可汗仍必须领导部众向农业社会掠夺,发展贸易,和徵纳贡赋,以期强化内部的团结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他个人以及统治氏族的权力基础。如可汗及统治氏族不能执行这些功能,游牧国家往往便会分崩离析,或回归到原有部族林立的状态,或以另一氏族为核心而形成一新的政治组织。有时,游牧国家又进一步自农业地区掳掠农民或工匠,或吸收战乱时华北的流民集团,在草原内部组成农耕及工艺制造的聚落。这种新生产聚落的形成,象徵著游牧国家本身的质变——从纯游牧国家到牧农政权。牧农政权的形成,不仅代表游牧国家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且促使可汗对内权力的绝对化,与对农耕国家的军事压力的持久化。
以农牧两种生产力为後盾,游牧国家往往能发动长期的掠夺战或征服战,以确保大量农产品和奢侈品的来源。如适逢中国内乱,而又有可资利用的官僚或地主,游牧国家便会不惜一战,在边境或中国内部设立傀儡政权。这种傀儡政权又往往是建立征服王朝的先声。所以,农耕社会的内乱便是游牧国家施行战争和征服的最好时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中国与外族盛衰的连环性,赖德懋所说中国的中央化( centralization )和地方化( decentralization) 与游牧社会的分散 (dispersal )与集中( concentration) 两个循环的相互呼应和陶恩彼所说的定居社会的内在失调足以将游牧民族拉进来,都是指此而言。
第七、在心理上,北亚游牧民族自古便感觉与中国各有不同的文化,不应服属於中国,而应分庭抗礼。这一观念无疑成为把他们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障碍,而致时服时叛。同时,游牧民族自古便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由此而衍生出主宰世界的普遍王权的观念。这一观念更导致他们屡次发动征服农业地区的战争。这是笔者一时想及,尚无学者仔细加以论证。所以较为详细地叙述於後:
汉初,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尚未制度化,匈奴与汉间的关系是建构在对等的和亲制上。老上单于致文帝书是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开端。文帝也答以:「皇帝敬问大单于无恙。」狐鹿姑致武帝书也说:「南有大汉,以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可见汉初匈奴一直以汉为对等,而汉廷也承认这一主权上的对等地位。宣帝时,呼韩邪虽纳贡于汉,但这一朝贡关系的建立主要由於双方实力的转变,并不反映匈奴对汉观念的更换,以後,八世纪时,薛延陀取代东突厥而成为漠北霸主,薛延陀的可汗曾明言:「我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俱一国主。」十七世纪初,察哈尔林丹汗( LegdonQan )也说过:「明帝为南方之主,我为北方之主。」可见游牧民族始终保持与中国对等的观念,并未因屡次迫於经济或政治原因,而向中国天子称臣纳贡以致有所改变。即使游牧国家与中国建立朝贡贸易的关系,有时游牧国家亦不自认为居於臣属的地位。譬如据中文记载,俺答汗( AltanQan )向明称臣并接受顺义王的封号。但蒙文史料却都说明室向俺答纳贡( albatatalgha ),这也是出於游牧民族的独立自主的政治意识。
这一与中国相对等的观念的形成,一方面由於游牧国家在军事上常可与中国相抗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游牧民族自古便有独立的文化和政治意识。汉文帝致老上单于书中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民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这种以长城为界「引弓之国」与「冠带之室」等两个文化世界相对立的观念,恐不仅汉人有之,匈奴人当亦有之。努尔哈赤( Nurhaci )复林汗书中也说:「且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 ...... 尔我异国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这也表示出北亚民族间自觉有共通的文化认同( identity), 而与中国和朝鲜相异。由这种独立的文化意识而产生独立的政治意识,觉得不应受制於中国,而应力争平等。王莽时匈奴协再「叛 ] ,便是志在恢复以前的平等关系。七世纪末,突厥骨咄录( Qutiugh )的举起反帜,结果摆脱唐的羁縻州县制度而建立突厥第二帝国,也是出於同样的原因。
游牧民族不仅有力求与中国平等的意念,而且有和中国天命思想相类似的王权神授的观念;并由王权神授的观念而发展出主宰世界的雄心。古来北亚游牧民族崇信沙蛮教,以天(突、蒙 tngri, 满 abka )为最高主宰。游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被认为系受天命而君临,拥有世俗和宗教双重统治权。中国的天命思想发展为普通王权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游牧民族的王权神授思想似乎也发展成主宰世界,创造世界帝国的观念,匈奴人是否曾有创造世界帝国的观念,虽不可知,可能为匈奴後裔的匈人( Huns )确实有此野心。匈人领袖阿提拉( Attila )便曾扬言他系受上帝之命而为世界之主。西突厥可汗室点密( D-ilziboulos=****** )也曾对拜占庭使者表示:据其祖先显示,突厥人征服世界时机已至。蒙古人更拥有宗教性的征服狂热,相信他们乃是承受「长生天」之命,「倚恃长生天的气力」而作征服世界之举。这种主宰世界,创造世界帝国的观念,固然可能是受到中国或波斯的普遍王权观念,或基督教世界教会观念的影响,但更可能直接由古代王权神授的观念衍生而来。
总之,由於生态系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游牧民族古来便产生独立的文化意识和自主的政治观念。而且这些观念持续不变,和中国近邻的农业国家高丽、安南等的情形有异。後者因与中国的生活方式相近,故为儒家文化所同化,因而易於纳入中国的世界秩序,以臣属的地位,与中国和平相处。北亚游牧民族则始终力求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地位,甚至想主宰中国,因而也引起很多战争。
以上所说是中外学者对造成游牧民族不时南侵原因的各种解释。从表面看来,这些说法不无相互矛盾之处。实际上,不过是各着重问题的一面,并非完全抵触。
最後,笔者试为融合上述各说,归纳出游牧民族侵略农业地区的一般因素:
游牧民族南侵的原因 , 深深植根於他们的经济体系之中。游牧经济有对自然变化的脆弱性,对农耕社会的倚存性和工艺文明的迟进性。对农耕社会的贸易与掠夺,是游牧民族解决经济问题的两个变换手段。从表面看来,无论为解决因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或为取得游牧社会所不生产的奢侈品,掠夺都不失为一捷便的手段。但通常只有在游牧民族本身有相当统一的政治组织,兵强马盛,而中国则在分裂状态,大难初定、或已由盛而衰的情形下,游牧民族始能发动有效的掠夺战争。少数为饥寒驱迫的游牧民,以血肉之躯与中国的强弩高垒相对抗的例子并不多见。和平的朝贡与贸易,则是游牧民解决对农耕社会经济倚存问题的另一方式。这种贸易的发展,往往有赖於武力为後盾,耍求贸易不遂,常迫使游牧民族发动战争。但贸易不遂不是造成游牧民族南侵的唯一原因,而游牧民族在武力上的优势,也未必是与农耕国家建立贸易关系的唯一要件。
除去这些经济因素外,游牧君长的对内政治设想和帝国意识,也是触动他们对外侵略的原因。就对内政治设想而言,对农耕社会的掠夺、贸易和战争,是游牧君长吸引部众,绝对化其权力的重要因素。就意识型态而言,游牧民族的独立主权与普遍王权的观念,常是促成他们与农耕国家发生冲突乃至发动征服战争的心理原动力。上述各种动机所触发的战争,可能是局部性的掠夺战,也可能全面性的征服战。战争性质的差别与规模的大小,不仅决定於动机的差别,而又决定於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双方的内在形势和相对的军事力量上。不过,征服王朝的建立则可看作上述各种动机的最高体现。就政治观点而首,征服王朝代表游牧君长权力绝对化与普遍王权观念的体现。就经济观点而言,则是游牧社会对农耕社会经济倚存的极限状态的实现——掠夺和贸易都出之於税收的方式。
(录自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民国六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萧启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