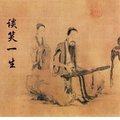四、所谓“主流认识”依据何在?
如上所述,认为炎黄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族的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族的文化,这虽然是极少数学者的观点和认识,但它却是从考古学文化的实际出发,结合古史传说、文献资料、经过认真研究和论证而得出的。相反,认为“五帝时代”即为龙山时代、黄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前虽然是学术界的主流认识并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所采用,但据笔者对最近十多年来我国最主要的一部分考古学期刊的了解,迄今都没有一个学者、一篇论文对黄帝时代、黄帝文化在龙山时代、龙山文化的时空范围内作过具体的研究和考证,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和意外!
将龙山时代视为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什么依据呢?如前所述,是因为龙山时代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古书上说“五帝”时期有“万邦”、“万国”,所以学者们感觉龙山时代“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甚至“感觉”也不要,直接将龙山时代说成对应于、相当于“五帝”时代,好象这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须证明的公理、常识。
实际上,除了陶寺文化被认为与尧、舜有关,这方面有一定的依据和论证外,黄帝、颛顼、帝喾对应于龙山时代的何种考古学文化,在学界基本上没有人论证,或者说没有有说服力的论证。据笔者所知,仅有个别“排排坐,分果果”式的牵强附会的分派或者臆测。比如蒋乐平先生认为传说时代的史迹与新石器时**古学文化相互印证而能够大致契合,甚至他还发现了这样的传说史迹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
蒋先生给出的传说中的“五帝”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是:华夏集团(河洛地区),炎帝为客省庄和三里桥类型龙山文化,黄帝为王湾类型龙山文化,共工为齐家文化,尧为陶寺类型;东夷集团(海岱地区),太昊为山东龙山文化,少昊为山东龙山文化,蚩尤为良渚文化;苗蛮集团(江汉地区),颛顼为下王岗类型龙山文化,帝鸿为石家河文化[32]。这个对应关系倒是将“五帝”中的三帝(漏掉了帝喾和舜),甚至包括炎帝、太昊全部按在了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但它仅有“发现”和安排而没有论证。
蒋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的衰落除了大洪水的原因外,还和黄帝杀蚩尤的战争有关,他说“如果将蚩尤看作是良渚文化的一个部落首领,那么这场大战正好作良渚文化因何在四千年前衰亡的注脚”。这似乎可以成为蒋先生持论的一个佐证。但是我们都知道,良渚文化是在距今约4200——4100年间衰落的,因此所谓“黄帝杀蚩尤”就应该是在良渚文化急遽衰落的晚期即距今4200年左右,这个年代还晚于陶寺类型即尧的年代(据《尚书·尧典》有关星象推算,尧的年代也在距今4300年前),显然乖谬太多。
将传说中的“黄帝”的年代定在距今约5000年有什么依据呢?司马迁的《史记》不列三皇,而将炎、黄排在《五帝本纪》之首,但他并没有明确黄帝的年代,甚至对颛顼、帝喾、尧、舜都没有纪年。这至少说明司马迁是拿不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年代的。现在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约4600年(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改为距今约5000年,显然与前述主流认识相关)。这个年代与辛亥革命有关。据《辞海》所附《辛亥革命时期所用黄帝纪元对照表》说明:“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广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民报》所用年代又据何而来呢?该报系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建立同盟会后所创办,因此宋健先生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一文中说《民报》所用黄帝纪元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33]。史式教授说其来源为: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
史式说,《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术数书,邵雍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甫谧则是一位精通针灸之学的医生,二人皆非史学家,所以“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1999)一共是4697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34]。
邵雍、皇甫谧二人皆非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否定黄帝纪元的理由,但黄帝纪元始于公元前2698年并非信史、缺少科学依据和充分论证是无疑的。因为:其一,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舜,不一定是象《帝王世纪》或其他史书所说的那样前后年代相接的帝王关系,而很可能各自代表着一个部落群体,是某一群体或其领袖人物公用的名号;其二,据神话学家袁轲研究,帝挚即少皋,二者实指同一人、同一部落群[35];其三,关于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的年代,不同的古代文献有不同的说法,《帝王世纪》仅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如《《春秋命历序》就与之不同》);其四,古书中所有关于“五帝”年代的记载均为文字时代古人的追记或推衍,没有确证,也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明。
宋健在《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中还提到另外两种黄帝年代,一是江苏的历史学家推算1911年是黄帝4402年,一是黄藻编辑《黄帝魂》定民国元年为黄帝4622年。杜正胜先生说:“古典文献对于三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很渺茫的,司马迁著史断自黄帝,根据传说世系推测,大约相当于典型龙山文化之始,不会超过西元前2500年以前”[36]。《竹书纪年》说黄帝在位100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63年、尧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共391年。许顺湛先生认为“《竹书纪年》所说的五帝年代,不仅不能与具体的人相对应,更不能与族团的情况相对应。惟一可供参考的是《纬书集成·春秋命历序》。
尽管《纬书》有许多不可信之处,但是《春秋命历序》谈到的五帝纪年,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春秋命历序》认为:黄帝、颛顼、帝喾是代表若干世,这个‘世’应理解为重要的领袖更替,而不是具体的一代人”。根据《春秋命历序》和夏代立国约距今4100年左右进行推算,许顺湛先生认为颛顼年代当始于公元前29世纪,即距今4900年左右,黄帝年代当始于公元前45世纪,即距今6420年左右[37]。而曹昱《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文中又有一说:“如果按近年史界对上古史断代的研究,以及按《通鉴外纪》所载《春秋命历序》所记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中,黄帝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3706——前3306年”[38]。
总之,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都是无所依据、未经论证的感性认识或想当然而已!
五、“主流认识”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
由于以上的原因,即人为地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将黄帝的年代估算在距今约5000年前,这种先验性的框架和东西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使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必然犹如戴着脚镣跳舞,甚至最终只能陷入困境、迷茫,当然这也是“探源工程”将要面临的问题。以下举例说明:
陈连开先生在《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中将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及其文化对应起来,但在该文中他同时又说:“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王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时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
我们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也有学者直接称为‘龙山时代’。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39]。这又是将黄帝时代、炎黄大战放在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采用的是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等同起来的流行说法。黄帝部族也许可以延续几千年,但我们又如何去研究“炎黄大战”呢?
“炎黄大战”总不可能纵贯两、三千年吧!何况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是很不相同的两个时代!更何况炎、黄文化在仰韶时代还有踪可寻,而在龙山时代具体与何种考古学文化相关,还渺无踪迹!史式先生在《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一文中追溯黄帝距今约五千年这种认识的来历,批评了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大约在五千年前,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制社会让位于父系制社会,青铜器与铁器先后出现。
这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个王朝”[40]。这里仍是将黄帝年代视为距今约5000年,采用的是流行的说法。陈连开、史式这两位对考古学文化或古史传说有所研究并有独立见解的学者,竟然一方面在发表自己不同于学术界流行的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等同起来、将黄帝的年代局限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认识,一方面又采用自己所否定或批评的这种流行观点说话,到底是习惯性使然还是害怕与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不同而遭到轻视或嘲笑?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在《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文章中将“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有关研究和讨论概括为四种观点:其一,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强调黄河流域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经过长期发展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二,认为中国约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进入文明时代;其三,认为中国在距今约5000年或5000年以前即已进入文明时代,其分析的具体个案,有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红山文化后期等,当时的主要特征是王权、神权在社会中居同等地位,出现了将两权集于一身的人物;其四,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由此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充分发展与繁荣时期[41]。
这四种观点中,唯有第三种观点才认为中国文明约在5000年前已经开始,但恰恰是据以产生这种观点的考古学文化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出现在辽西、内蒙古地区(红山文化)、山东和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地区,而它们恰恰与传说中的黄帝没有多少关系。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大都在中原一带,如陕西黄帝陵、姬水、洛水、炎黄二帝同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河南的新郑(有熊)、灵宝(铸鼎原)、首山、荆山、鼎湖等,北部接近长城地带的仅有河北涿鹿。如果把黄帝的年代确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或者限于龙山时代,那么它不仅不能与考古学文化相契合,而且也不能与有关传说和遗迹相契合,因为陕西、河南与黄帝传说有关之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
或许为了要寻求一种与黄帝距今约5000年这种说法相适应的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有的学者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如苏秉琦先生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42],韩嘉谷先生认为黄帝早期活动区应是红山文化分布区,“黄帝成为《史记·五帝本纪》的第一人,极可能和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南下有关”[43]。但是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南下最南不超过河北中部,根本没有到达中原,那么中原一带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又如何解释呢?
另一个问题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碰撞的接触地带在河北北部,如果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那自然应该将庙底沟类型视作炎帝和蚩尤文化。但是就红山文化与庙底沟类型而言,是后者北上影响了前者,而不是前者南下影响了后者,这与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的古史传说是完全相背的,所以将红山文化视作黄帝文化是有问题的,或者说红山文化肯定不是黄帝文化。那么距今5000年的黄帝的考古学文化又到哪里去找呢?
199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河北涿鹿县人民政府在涿鹿联合召开“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提出的一个有关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的问题颇发人深思:“炎黄在渭水一带,处于黄汉中游,而蚩尤部族源于下游,而最后均打到河北一带,虽然可能经过联合再内战分开,但打仗需要后勤才能远离部族原地。实际后黄帝取胜后将政治中心建于涿鹿。问题在于为什么夏商开始到秦汉政治中心又到了黄汉中游呢?线索尚无”[44]。李先登先生在《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文中说:“在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时代)之初,中国大地开始了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
当时主要是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斗争,最初东夷强大,反映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繁荣与西扩,经过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族团的一部分开始融入炎黄集团,出现了人类学上所说的酋邦,而东夷族团的另一部分南迁为后世的三苗”[45]。问题之一: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接触地带是豫东、鲁西南、安徽北部和江苏西北交汇之地,怎么打仗又打到了河北的涿鹿?问题之二: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和西进在其晚期达到高潮,对此学者已有详尽的研究[46]。栾丰实先生说:“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加强,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逐渐形成一股潮流。
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8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此后一直到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初,除了龙山时代末期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对东方的影响稍占优势之外,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47]。即是说,黄帝打败蚩尤应该是在距今约4600一4500年这段时间,而此期正是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北上在河北北部与红山文化碰撞再南下在山西南部形成陶寺类型的时期。这种认识不仅将黄帝之后的少昊、颛顼、帝喾全都挤掉了,而且更与古史传说和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相悖。
因为大汶口文化与少昊部族相关在学界几乎已成为定论,在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年代排在少昊之前,炎、黄、蚩之战不可能在少昊的末期。问题之三,在东夷文化大肆侵入中原,南方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北侵威胁的龙山时代,黄帝怎么会远离中原,跑到河北涿鹿去建立政治中心?